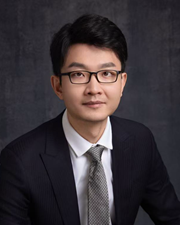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民事訴訟中“給經營者造成直接損害”的證明問題探析
作者:丁華 黃威 孫東順 李棣森 2019-11-14內容提要:在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案件的民事裁判中提涉了“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這一構成要件,但司法實踐領域目前均未對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是否需要證明“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以及如何證明的問題形成一致的意見。本文結合法律法規規定、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相關民事裁判案例和律師代理實務對“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的證明問題進行了探析。
關鍵詞:虛假宣傳 不正當競爭 無關誤導性后果
一、問題的提出
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行為規定在《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經營者不得利用廣告或者其他方法,對商品的質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產者、有效期限、產地等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的構成要件,最高法院曾經歸納為(1)經營者之間具有競爭關系;(2)有關宣傳內容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3)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1]但近年來的司法實踐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的認定事實上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觀點,其中焦點主要集中于上述第(3)項構成要件,即“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是否需要證明以及如何證明的問題。對此,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以下三種觀點:
(一)原告需證明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
目前的司法實踐中已存在很多案件,原告已經成功證明案件滿足“經營者之間具有競爭關系”,以及“有關宣傳內容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這兩個構成要件,但法院仍以被告的行為不滿足“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要件為由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這其中最著名的案件便是最高法院2009年10月判決的攜程與黃金假日虛假宣傳糾紛上訴案(下稱“攜程案”)[2] 。在攜程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對此,該二被上訴人(指攜程)在經營中對各自的身份表示確有不當之處,有混同使用或者模糊稱謂其經營主體身份的行為,……上訴人(指黃金假日)并未舉證證明該二被上訴人的有關行為包括上述誤導性后果使上訴人自身受到了直接的損害,不能簡單地以相關公眾可能產生上述與上訴人無關的誤導性后果而代替上訴人對自身受到損害的證明責任。……”攜程案之外,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也作出過類似判決,甚至直接在判決書引用了攜程案的說理。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年8月判決的深圳房金所金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等訴上海新居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下稱“房金所案”)[3]中,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指出:“……因此,上海新居公司在其對外宣傳中對其控股股東的介紹確有不當之處,可能造成相關公眾對上海新居公司股東身份的混淆或者誤認。但是,不論相關公眾是否會對上海新居公司股東身份產生混淆或者誤認,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并未舉證證明上海新居公司的上述宣傳行為包括上述誤導性后果使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自身受到了直接損害,不能簡單地以相關公眾可能產生上述與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無關的誤導性后果而代替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對自身受到損害的證明責任。……”
通過攜程案及房金所案不難看出,房金所案的說理與攜程案一脈相承。并且,筆者在代理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案件時獲悉,房金所案在2016年至2018年期間成為上海法院系統在處理類似案件時的重要指導。
(二)原告無需就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進行證明
與上述攜程案及房金所案不同的是,最高院近年來在部分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糾紛的審理中,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的認定并未要求原告就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進行證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裁定的加多寶(中國)飲料有限公司、廣東加多寶飲料食品有限公司與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案[4](下稱“加多寶案”)。
在加多寶案中,加多寶中國公司和廣東加多寶公司使用涉案廣告語“加多寶涼茶連續7年榮獲‘中國飲料第一罐’”“加多寶涼茶連續第六年蟬聯‘中國飲料第一罐’”“加多寶連續7年榮獲‘中國飲料第一罐’”“加多寶榮獲中國罐裝飲料市場‘七連冠’”“中國第一罐”“第六次蟬聯‘中國飲料第一罐’”的行為是否構成虛假宣傳行為系本案較為重要的爭議焦點之一。對此,最高院在本案的裁定說理部分中指出:“從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虛假宣傳的目的看,反不正當競爭法是通過制止對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宣傳行為,來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一方面,從不正當競爭行為人的角度分析,侵權人通過對產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宣傳,如對產地、性能、用途、生產期限、生產者等進行不真實或者片面的宣傳,獲取市場競爭優勢和市場機會,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利益;另一方面,從消費者角度分析,正是由于侵權人對商品或者服務的虛假宣傳,易使消費者發生誤認誤購,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利益。因此,從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虛假宣傳的目的看,其并不以被侵權人的直接損害為要件判斷虛假宣傳行為是否成立。”
對于最高院上述所指出的“不以被侵權人的直接損害為要件判斷虛假宣傳行為是否成立”,雖然虛假宣傳行為的成立并不意味著行為實施者必然承擔民事責任,亦即最高院的上述裁定中的論斷亦并未明確否定“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這一構成要件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認定的必要性,但筆者認為最高院對于性質屬于民事案件的加多寶案裁定中闡釋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了另一種司法觀點,即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構成的認定,應當結合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虛假宣傳的目的綜合考量,不應拘泥于文首所提及的“三要件”的文義,而對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糾紛的原告提出過高的舉證責任要求。
(三)以“受損可能性”標準取代“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的證明
針對上述兩種對立觀點,司法實踐領域亦有第三種觀點。一方面,如果如上述第一種觀點,要求原告必須證明被告的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方可認定被告的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行為,則將會難以避免地造成過分加重原告舉證責任的問題;而如果如上述第二種觀點,即在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糾紛的審理中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無需原告就被告的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進行證明,則侵權構成要件中缺失了“存在損害”這一構成要件,直接認定侵權成立仍然有失偏頗。因此,部分司法界人士建議采取“受損可能性”標準,即“作為原告的經營者由于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其競爭優勢可能被削弱、其交易機會可能受干擾、其市場份額可能被侵占。從結果上看,所謂的損害既可能是市場份額的縮減,也可能是商譽受到損害(市場評價降低),只要原告能夠證明其權益因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可能受到損害,即應認為已滿足損害結果及因果關系要件”[5]。
例如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于2018年審結的崔衛榮與南京我樂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6](下稱“歡樂頌案”)中,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認為,“要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的虛假宣傳行為,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應當滿足如下條件:一是主觀上存在與其他競爭者進行不正當競爭的故意;二是客觀上對商品或者服務的相關信息做了內容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宣傳;三是效果上宣傳行為造成了欺騙、誤導消費者的后果或者可能性”。
對于上述三種司法觀點,筆者認為均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不足之處,具體如下:
第一種觀點要求原告需證明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這無疑向原告施加了過重的舉證責任。在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案件司法實踐中,“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構成要件的舉證一直是原告在訴訟中的痛點,往往很難舉證證明,原因在于在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案件中,雖然原告確實遭受了實際損害,但這些損害往往并不直接體現為原告的經濟損失,即便真的導致了原告的經濟損失(例如客戶流失導致的收入減少),由于虛假宣傳侵權行為的特殊性,原告也很難證明經濟損失與被告侵權行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另外對于司法判決中提及的無關的誤導性后果也缺乏明確的判斷標準和指引,不利于對此類案件進行規制,實踐中難以操作。
第二種觀點認為被告的虛假宣傳行為“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是一種不證自明的事實,無需證明,筆者認為此種觀點處理方式過于簡單,沒有針對具體的情況進行甄別,同樣有失偏頗。
對于第三種觀點,筆者認為其實質上系對于前述兩種觀點在舉證責任方面進行了一種程度上的折中,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原告的舉證責任,更為公平合理,然而采用這種或然性的模糊標準,既有法理依據不足的問題,也難以成為清晰明確的規范此類案件裁判的指引。
針對上述三種觀點所存在的不足之處,筆者從侵權行為構成要件的角度出發,認為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糾紛中,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原告仍應就其“直接損害”進行證明,但鑒于該證明在客觀上的難度,可以嘗試將證明原告的“直接損害”這一問題進行轉化。筆者的觀點是,只要有虛假宣傳行為,就一定會產生誤導性后果,這是不言自明的、無需論證的,但是誤導性后果的存在并不意味著該誤導性后果與原告有關聯,也就是說該誤導性后果的作用對象不一定為原告,或者對原告的作用微乎其微,因此筆者認為可以通過證明誤導性后果與原告(受害方)有關,即通過對“有關的誤導性后果”的證明,實現對被侵權人的“直接損害”的證明。對于這個問題,攜程案及房金所案判決雖然均提及了“無關的誤導性后果”的概念,但最高法院和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在兩案的說理部分沒有進一步對“無關的誤導性后果”和“有關的誤導性后果”的判斷標準進行進一步的闡釋和說明。筆者認為,這可能會導致實踐中的分歧和爭議,特別是房金所案在攜程案之后成為上海法院系統類似案件指導案例的情況下,更有必要厘清“無關的誤導性后果”和“有關的誤導后果”的判斷標準。筆者曾代理過數起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訴訟案件,并就此類案件進行了探索性研究,現結合自身辦案體會及相關判例,嘗試對該“無關的誤導性后果”和“有關的誤導后果”的判斷標準問題進行探討、分析。
二、第一順位的判斷標準:是否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
筆者認為,誤導性的宣傳是否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是判斷誤導性后果是否與原告有關的首要判斷標準。即如果誤導性的宣傳并未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則可以直接認定誤導性后果與原告無關,不存在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侵權;如果誤導性的宣傳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則再進入后續判斷(見本文第三部分)。
筆者將是否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首要判斷標準的原因是,即便行為人的宣傳行為存在誤導性后果,但是如果該宣傳沒有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那就屬于正當的市場競爭。事實上,正當的市場競爭也會導致競爭對手的利益受損,只不過這些利益受損并不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損害。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的原則性規定,“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遵守法律和商業道德。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本法規定,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便不難看出,“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和“遵守法律和商業道德”其實是一體兩面,“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本就是商業道德的一部分,而該等原則也往往是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原則,也即變成法律要求。如此看來,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行為人損害的必須是其他經營者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合法權益,而經營者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的合法權益是否遭到損害,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判斷標準就是行為人的宣傳行為是否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
上述分析在司法實踐中的直接體現便是攜程案。該案中,攜程商務公司是“攜程網站(www.ctrip.com)”的合法經營人,攜程商務公司在“攜程網站(www.ctrip.com)”發布旅游產品信息,攜程計算機公司是“攜程CTRIP”商標注冊人,攜程計算機公司通過“攜程網站(www.ctrip.com)”開展機票預定業務。攜程商務公司和攜程計算機公司在對外宣傳中大量混同使用“攜程”和“攜程旅行網”的簡稱。對此,最高法院認為“該二被上訴人(指攜程商務公司和攜程計算機公司)在經營中對各自的身份表示確有不當之處,有混同使用或者模糊稱謂其經營主體身份的行為,如大量使用“攜程”和“攜程旅行網”的簡稱,有關的宣傳容易使人產生對市場上的“攜程”是否是一家、“攜程”到底是指誰、“攜程旅行網”到底是誰在經營等疑問和困惑,可能會造成相關公眾對該二被上訴人身份的混淆或者誤認。”但最高法院最終認為,該混淆或者誤認與上訴人黃金假日公司無關,從而未認定攜程商務公司和攜程計算機公司構成虛假宣傳。
雖然最高法院沒有給出明確的判斷標準,但仔細分析攜程商務公司和攜程計算機公司的行為不難看出,二者在對外宣傳中大量混同使用“攜程”和“攜程旅行網”簡稱,其實并未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原因在于,集團公司或者關聯公司在商業活動中混同使用主要商標或字號的做法非常普遍,早已成為社會公眾所接受的商業慣例,并無任何不正當之處。例如平安集團內部的平安保險公司、平安醫療保險公司、平安銀行等公司在對外宣傳時,都或多或少存在簡稱為“平安”的情況,雖然可能會造成一般人對于該等主體身份之間的誤解或混淆,但這并不會損害其他公司的合法權益。究其本質,在于“平安”二字作為知名字號及商標,屬于知識產權的一種,平安集團本來就可以將這些知識產權授權給集團內部的公司使用,從而給集團內部的公司帶來商譽和競爭優勢,平安集團的這些做法無可厚非,無論是在商業道德上還是在法律上并無任何不妥。
因此,筆者認為誤導性的宣傳是否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是判斷誤導性后果是否與原告有關的首要判斷標準。
三、第二順位的判斷標準:宣傳內容與原告關聯性的緊密程度
筆者認為,在誤導性宣傳已經違反法律和商業道德的情況下,并不必然導致對于原告的損害。這時,還需要判斷誤導性宣傳內容與原告關聯性的緊密程度,分為如下四種情況。
(一)誤導性宣傳內容直接針對原告
誤導性宣傳內容直接針對原告是指在誤導性宣傳中,直接、明確地提到了原告的名稱。筆者認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一般可以直接認定為誤導性宣傳損害了原告合法權益。
比較典型的案例是筆者曾辦理的學而思訴樂課力等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案[7]。在該案中,樂課力作為學而思的競爭對手,在其師資介紹的資料中宣稱絕大多數老師為“原學而思頂級明星老師”、“原學而思小升初名師”,在課程內容的介紹資料中宣稱課程大綱主要參考“學而思思維匯編”等資料,在學校概況的介紹中宣稱“樂課力培優是由原XRS頂級老師組建”,在多篇講座推薦的資料中宣稱樂課力系“諸多原XES頂級老師組建”。然而事實上,雖然樂課力介紹的相關教師曾在學而思任教,但這些教師并非是所謂的頂級明星老師、頂級老師。鑒于被告誤導性宣傳中,直接、明確地提到了原告字號和商標或其簡稱,屬于直接針對原告的虛假宣傳,因此該案審理法院認為樂課力構成虛假宣傳,侵害了學而思合法權益,構成侵權。
(二)誤導性宣傳內容間接針對原告
誤導性宣傳內容間接針對原告是指,雖然宣傳的內容沒有直接、明確地提到原告名稱,但是通過宣傳內容可以直接指向原告或者包括原告在內的少數幾家經營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也可以認定為誤導性宣傳損害了原告合法權益。
例如,筆者正在代理的一起虛假宣傳案件中,侵權方雖然沒有直接在宣傳中提到筆者當事人的名稱,但是侵權方宣傳的內容包含筆者當事人的客戶、成功案例以及筆者當事人的某一資質,并且筆者當事人是亞太地區唯一獲得該資質的企業。筆者認為,通過這些信息很容易判斷出侵權人的宣傳是針對原告所為,產生的誤導性后果明顯同原告相關,損害了原告的合法權益,應當被認定構成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侵權行為。
(三)較強的市場相關性
在誤導性宣傳內容沒有直接或間接針對原告時,如何判斷是“無關性誤導后果”還是“有關性誤導性后果”?筆者認為,這需要判斷原被告之間市場的相關性,如果雙方之間市場具有較強的相關性,則侵權方的誤導性宣傳就很有可能屬于損害到原告的合法權益的“有關性誤導性后果”。
筆者進一步認為,在判斷市場相關性時,可以通過原告的知名度、原被告之間的競爭關系、原被告地域上的遠近、宣傳的內容等要素進行綜合判斷。例如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判決的上海百花教育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下稱“百花公司”)與上海卓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下稱“卓基公司”)、胡麗萍等侵害經營秘密糾紛(下稱“百花案”)[8],卓基公司在網站和宣傳冊上宣傳的與日本教研院的合作和98%的名校錄取率等內容均無事實依據,但并未直接或間接涉及百花公司,但法院仍認為“……其行為易使相關公眾誤認為卓基公司具有較強的教育資源和擁有境外知名教育機構合作伙伴,這種對外宣傳的效果在招生時會比同為從事幼升小教育培訓的百花公司取得更多的競爭優勢,影響到百花公司業務的發展,損害了百花公司的利益,構成虛假宣傳,應當承擔停止侵權、消除影響和賠償損失的民事責任。”
筆者認為,法院之所以在卓基公司宣傳內容未涉及到百花公司的情況下做出侵權判決,原因在于考慮到了百花公司是知名教育培訓機構,百花公司與卓基公司之間具有直接的競爭關系,并且兩公司的地域范圍都在上海市,因此原被告之間具有較強的市場相關性,被告的誤導行為損害原告在該市場中的競爭權益具有高度的蓋然性。考慮到前述情況,即便是卓基公司在宣傳中沒有點名或影射百花公司,但卓基公司通過虛假宣傳虛增競爭優勢的同時,勢必影響到百花公司的招生,損害了百花公司合法權益。
(四)較弱的市場相關性
筆者認為,如果雙方之間市場相關性較弱,則侵權方的誤導性宣傳就難以損害到原告的合法權益。原因在于,如果原告的知名度本就較弱,在市場中的存在感不強,或者原被告雙方地域市場相去甚遠,那么很難認定侵權方的行為能損害到原告合法權益。因此在筆者看來,雙方之間市場相關性較弱的情況不宜通過民事法律關系進行調整,而交由行政手段進行規制更為適宜。
比較典型的案例便是房金所案。在該案中,上海新居公司在對外宣傳之中,僅憑其自然人股東在新浪公司任職,便宣傳其股東為新浪公司,遭到深圳房金所公司指控虛假宣傳。上海知識產權法院認為:“……上海新居公司在其對外宣傳中對其控股股東的介紹確有不當之處,可能造成相關公眾對上海新居公司股東身份的混淆或者誤認。但是,不論相關公眾是否會對上海新居公司股東身份產生混淆或者誤認,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并未舉證證明上海新居公司的上述宣傳行為包括上述誤導性后果使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自身受到了直接損害,不能簡單地以相關公眾可能產生上述與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無關的誤導性后果而代替深圳房金所公司、上海房金所公司對自身受到損害的證明責任。”由此可見,上海知識產權法院實際上已經認定上海新居公司宣傳相關知名公司為其控股股東的行為有不當之處,但卻未作出侵權判決。筆者認為,很有可能是法院認為上海新居公司與深圳房金所公司之間的市場相關性較弱,在“侵權”發生之時,上海新居公司的不實宣傳的誤導性后果難以作用于深圳房金所公司,難以認定對深圳房金所公司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
四、結論
綜上所述,在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民事訴訟案件中,筆者認為對于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虛假宣傳行為構成的認定中,對“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這一構成要件的證明可以通過證明誤導性后果與原告(受害方)有關而實現。對“無關的誤導性后果”和“有關的誤導性后果”的判斷標準為:應當首先從是否符合法律和商業道德角度對涉案的誤導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判定;在判斷誤導行為違法后,再進一步客觀分析涉案誤導行為的針對性和原被告雙方的市場相關度,最終對該涉案誤導行為后果是屬于“無關的誤導性后果”還是“有關的誤導性后果”做出判定,從而解決虛假宣傳不正當競爭民事訴訟案件中是否“給經營者造成了直接損害”的證明和裁判問題。
五、參考文獻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09)(法〔2010〕173號)[R].北京:最高人民法院,2009。
[2]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黃金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與攜程計算機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攜程商務有限公司、河北康輝國際航空服務有限公司、北京攜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上訴案(2007)民三終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北京:最高人民法院,2009。
[3]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深圳房金所金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等訴上海新居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2016)滬73民終107號民事判決書.上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
[4] 最高人民法院. 加多寶(中國)飲料有限公司、廣東加多寶飲料食品有限公司與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案(2015)民申字第2802號民事裁定書.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2016。
[5] 徐卓斌. 虛假宣傳的侵權構成如何認定. 上海: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
[6]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 崔衛榮與南京我樂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2018)滬73民終284號民事判決書. 上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8。
[7] 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上海學而思教育培訓有限公司、上海閔行區學而思進修學校、上海長寧區學而思進修學校與上海樂課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樂課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著作權侵權糾紛、不正當競爭糾紛案(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1324號民事判決書.上海: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2016。
[8]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上海百花教育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上海卓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胡麗萍等侵害經營秘密糾紛二審(2015)滬知民終字第643號民事判決書.上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案件年度報告(2009)(法〔2010〕173號)[R].北京:最高人民法院,2009,第25條。
[2] 最高人民法院.北京黃金假日旅行社有限公司與攜程計算機技術(上海)有限公司、上海攜程商務有限公司、河北康輝國際航空服務有限公司、北京攜程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上訴案(2007)民三終字第2號民事判決書.北京:最高人民法院,2009。
[3]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深圳房金所金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等訴上海新居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等不正當競爭糾紛上訴案(2016)滬73民終107號民事判決書.上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
[4] 最高人民法院. 加多寶(中國)飲料有限公司、廣東加多寶飲料食品有限公司與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廣州王老吉大健康產業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案(2015)民申字第2802號民事裁定書.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2016。
[5] 徐卓斌. 虛假宣傳的侵權構成如何認定. 上海: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
[6]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 崔衛榮與南京我樂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虛假宣傳糾紛(2018)滬73民終284號民事判決書. 上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8。
[7] 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上海學而思教育培訓有限公司、上海閔行區學而思進修學校、上海長寧區學而思進修學校與上海樂課力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樂課力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等著作權侵權糾紛、不正當競爭糾紛案(2015)徐民三(知)初字第1324號民事判決書.上海:上海市徐匯區人民法院,2016。
[8] 上海知識產權法院.上海百花教育信息咨詢服務有限公司與上海卓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胡麗萍等侵害經營秘密糾紛二審(2015)滬知民終字第643號民事判決書.上海:上海知識產權法院,2016。